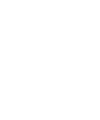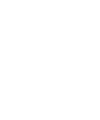陋篇(古言,NP) - 火星
礼盒送来,盛着山楂。
文鸢病后,没什么食欲,这份礼物来得正好。
送礼的人是一位小丞,皇家私库少府的属官。
“臣郤梅敬。”“多谢少府。”
病中太多礼物,堆在角落,其中大半都是食物。宫人担心是否会生虫鼠,文鸢就让他们启封吃了,自己没动。
这么多天,她还是第一次吃下官的敬礼。
使女们都来帮忙冲洗:“山楂可口,果然公主喜欢,无愧世代为卿,郤梅大人真贴心。”
欢笑并人声,被来人打断。
“文鸢,听说你病了。”
臧复在门外,迟迟不敢进来,怕一室都是女子。文鸢称“燕王”。他原地不动,局促地笑:“打扰你。”
使女们初见臧复,被震慑:他一身挂两印,极人臣的六郡之王,又是无虑狼水养出的男儿,连头发都打卷。
两边互相害怕。文鸢刚请臧复入室,使女就列队走了。
臧复有点尴尬,坐文鸢脚边。
“你来省?”
“很久不见,来看看你。”
“但叁月一朝,你上月才来,还和我同游兔园。”
“啊啊,”臧复面红耳赤,言不达意时,就比划起手,“对了,小玫,小玫让我问候你,她听说你病了,本来也要与我一同入省,说要亲手为你煮水。但中山侯处正在发水,冲得不像样,她还是帮她父亲去了。”
话说到这,两人一起吃山楂。室内细细的咀嚼声。
“臧复,为什么要骗我。”文鸢小心地问。
臧复大惊诧:“我没有。”
“中山接广阳,地高而几水共流,一地发水,殃及另一地,小玫去救涝,你应去救涝与漱啮(侵蚀),比她更忙,”文鸢看他那样窘迫,声音越来越低,“然而你现在省中。”
“文鸢你,你聪明,骗人是我不好,”臧复垂头丧气,几次张口,耳朵都红了,“这是,怎么说,于你是件愤然事,我想着如何才能告诉你,而你不气。”
隐语在扶风某城响起时,右扶风言拱正与儿子对弈。
“叁辅长官是不用操心这事的,”自家檐下,言拱畅谈,“且不论其他,我们那位陛下喜爱燕风女子,左右京的好女通通动不了他。”第二天,言拱的话被人上报。
右扶风罚斛以外,许多人注意到话的中心:燕风女子。
新官们又来劲头:“我皇这不是也有所爱?”多少奏书堆上息再案头,内容都差不多,请皇帝陛下择燕六郡贵女,行人伦,衍子孙,去隐语。
他们百折不挠,心想这方法不通,再行谏诤。没想息再答应了。
“让燕王亲自来送,我有话说。”
臧复广阳治完水,上城看百姓,正在欣慰,却接了省中戒。
他做梦也想不到,息再会让他送女人。
“戒书指责我不尽臣道,说君有求而臣不应,责我这月就送燕女来朝,还有要求哪,要身高丰腴,貌美胆大,”臧复都要哭了,“文鸢,文鸢,我对不起你,我该先与你书,问问你的意见。”
文鸢吃山楂:“问我?”
“你不是爱陛下?”
文鸢呛得鼻酸。臧复送水,正想说些安抚的话,殿外有人叫他:“臧复。”
能直呼臧复姓名者,省中一人而已。文鸢让他快去:“语气不好。”臧复又怕,又不平,跟着去了殿上,听他说有事,便失望地说:“事毕,女子都已送到。”抬头就见息再的笑。
他正在玩弄火石,打出火星,片刻后,笑着骂人:“傻东西”
臧复愣愣的,被他招去面前,授一枚符。
“这是修太尉与其弟的虎符,重做了,用来调遣燕赵兵马,你收好,与你的太尉符放在一起。”
臧复的情绪尽散:“有变事?”
息再摇头:“这次你来省有名,返回时不用赶,绕点路,去看看豫靖侯,并几位王侯,下月无论有事否,以兵马禁其私出境。”臧复明白,想起对文鸢的话,又有些惭愧。
不过息再严令保密,他只好不告而别,带上燕女,当是带她们旅行。
老鼠抱火石,从门前过。
使女怕得不行,在文鸢怀中瑟瑟。
“果然生老鼠了!求公主换一处居室,求公主,不然就让我们走吧。”
文鸢听宫人哭了一夜,第二天去见小茅。
小茅眼看别处:“实话说吧,昨夜宫中各处都有老鼠抱火石,真是天生异象。若它们联手打火,则省中再无安全。不过公主宽心,茅宫令一定给公主找好住处。”
文鸢说第二遍,自己不想搬走,请小茅安顿使女。小茅装没听见,径直去前殿复命了。
第二天,文鸢被车载到天数台。
“世母处有会打火的老鼠,儿子已听说了,还写书请世父责罚守宫,”千秋与文鸢同行,“天数台不曾有这种东西,有了,矩父也会驱散。世母先住下,等宫室整顿了,再回去。或者就住在这儿吧。”
迁居公主,被视为一种手段。
省中都在分析,或说皇帝终止不兄之行,或说皇帝幸燕女,将为人父……好在天数台清净,文鸢没听到多少。
她只是一头雾水,空闲时,常去原来的宫室,在栏柱间寻找:“什么打火老鼠呢。”
“请公主回天数台。”汲怿说。
文鸢每受惊吓,猛回头,他都漠然。
两人一前一后走。文鸢看地上的长影,伴生一样笼罩自己。
“你不必等我,要教千秋,就先去吧。”她以为他往天数台,是偶遇自己。
“专程来接公主。”
“你受命看护我?”
汲怿正色:“住别处,则小臣不会过问,最多阶下叩首;同住天数台,没有上命,也要看护公主起居。”
话说得好,然脸色很差——他俯视文鸢,带些傲气,意为不要多想。
文鸢连忙点头。
其实不算同住,一天当中,汲怿在天数台仅一时二刻,教完就走:他毕竟由息再提为尚书,虽然被迫与紫骏竞争,失了官,每天依旧很忙,去中朝、去前殿、回自己的官庐睡觉,只有一天破例。
一天黄昏风雨。
待诏走完,天数台剩了旗帜,已经淋倒。水下高台,卷折黄土,花草覆灭。文鸢熄灯,暗昧中睁眼。
到今天,她与常人无异,没有灯火,几乎不能识物。她也不爱黑天,有使女陪伴,就点铜枝最多的大盏,把室内照得光辉明亮。但独处时,她总还会这样待着,四周越黑,她越舒畅,至于自己都怪恶:上瘾一样。
所在的夹室背阴,很静,文鸢听着自己的呼吸,几乎要睡。
“……父。”
是千秋,文鸢想。
闪电半刻才下,父声还在。
文鸢细听,以为千秋在廊中。
或许千年目盲不察,千秋溜出去玩了——文鸢还记得他父子相处的活泼。
她循声出来。
其实,千秋在房间,朗诵刚到手的孝经:“师父选段,资于事父以事母……资于事父以事君……兼之者父也……父……”
天数台夹室、个室连环,回声不小。只是文鸢没住过,不知道。
廊上灭灯。挂帘被吹湿。大雨内外徘徊。
文鸢上台,看没有人,知道误会了,便要回去。
闪电把汲怿打亮。
文鸢只看清黑白分明的眼睛,吓得踩错一级,去扶栏杆。
他已经在她身前。两人贴着,一人抓住另一人的手,很快都湿透。热的雨水流向谁的手腕。
“你怎么?”
“你流血了。”
他抓着文鸢,连她的热血一并抓在手里,去空台观。
观榭开阔,能见平原以外的光。文鸢因此看清他的脸:“这样大的雨,你……”
“与小殿下相约,教授本经,迟到了。”
“但狂风暴雨。”
“与小殿下相约,教授本经,迟到了。”
他开合嘴巴,像个偶人,同时撕开里衣,包住文鸢的擦伤。天候狂暴,他的动作很轻。累筑的高台都在战栗,文鸢由他禁锢,却动也动不了。
“汲怿?”
汲怿立刻松手。
文鸢擒住袖,帮他擦血,也被拒绝。
雨会冲洗,他说,并拿不染血的手向外挥一下。
乌云压夜,汲怿湿衣湿发,在省行走。
宫道无人,驰道无人,素砖只有他的官靴踩过。
离庐舍还有几十步。汲怿扶着树,不走了。
另一只手被他裹在袖中。
某一刻,他甩开袖子,把手往嘴里塞。
“是谁?”
“是我。”汲怿放下手。
郎中夜里巡门,碰到汲怿,彼此见礼,过后对郎官们说:“陛下爱臣,果然落落有度。”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